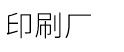印刷術背后的文化史:作為批評的考證
發布時間:2024-03-24 點擊:226
考證,常被視為文史研究中尋獲真相的最基本方法,不過運用得當的話,它有時也可以成為有力的批評,借以讓人反思舊有的方法和觀念。讀完《中國印刷史研究》,給我印象更深的,與其說是他以獅子搏兔之力考證得出的結論,倒不如說是他在考證過程中展現出的對舊有學說及其方法論的犀利批評。就此而言,本書不應被僅僅視為“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倒不如看作是對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批評,只不過選擇了中國印刷史作為切入口。
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僅僅是對這種科學技術發明或其社會傳播過程的客觀論述,因為長久以來,“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一直是我們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無人敢于質疑這一神主牌,相反,正如在其它諸多科技發明的論述中時常見到的那樣,國內學者通常會習慣性地加上一句“比西方早了若干年”這一短語來增強我們一度受損的自信心。
由于結論已經預設好,因此人們常常無暇去仔細推敲每個細節證據,稍有一點能和預設結論相聯的資料,都被迫不及待地拿來作為支撐那個龐大架構的材料。這在心理學上稱之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bias),即當你相信一個事物之后,就會主動尋找能夠增強這一信念的信息。這有時還會導致一種奇怪的現象,就像在西方學者質疑“馬可路波羅究竟是否到過中國”(更多是為了通過這一設問來展開相關問題的討論)時,為這位信口開河的意大利探險家竭力辯護的卻是中國人,原因恐怕或多或少是因為他已被視為“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那他就非到過中國不可。印刷術研究也不例外,一如書中所言,“在研究印刷術起源問題時,有相當一批人都是以捍衛中國人的發明權作為研究目的”。
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吳魯旺(den-nish.wrong)曾說的,脫離了問題,答案是沒有意義的。但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中,人們往往太過注重“答案”而很少去想“問題”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于論證的過程也是走過場,因為他心里已經有答案了。這在學術研究中造成了一系列遺留至今的問題,諸如:先入為主的預判或“定調”;想當然的設想、推導,而忽略邏輯論證;樂于采信符合自己預期的薄弱證據乃至錯誤論證,但忽視或淡化對自己結論不利的證據;采納不夠可信的第二手、第三手文獻,甚至將明知已被證偽的材料仍用作論據,只因這些有利于推導出自己的結論;只看孤證,而不顧及深遠的歷史驅動力及其邏輯性;急于自樹新見,而缺乏與學術共同體的對話,甚至在遭遇質疑后仍各執己見……凡此等等,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都可找到。辛德勇先生在書中多次強調受“正規文史訓練”的重要性,但這些問題的根源或許更可能是思維定式,以及國內文史訓練注重解讀材料而偏廢純理性的邏輯思辨。
書中關于銅活字的考證在這方面可謂典范。辛氏以扎實的文史功底,證明所謂明代銅活字印書,其實根本沒有任何可靠記載,“事實上根本無法認證它的存在”,而我們理應承認朝鮮在活字印刷上比中國先進。在此,他詳細辨析了古籍中“活字銅板”、“銅板活字”和“銅板”等記載,主張這只能解讀為是“活字印本在印制時采用了銅質版片來承放字釘,而根本沒有涉及字釘的材質;據此推定的所謂明銅活字印本,當然完全不能成立”。在此,考證在摧破舊說的過程中,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批評方法。
在以往對這類發明權的研究中,還存在一個不自覺的傾向,即“越早越好”。盡管這有時也是與學者們對材料的不同解讀所致,但恐怕也是這種心態才促使人們去相信一些不可靠的孤證。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辛德勇反復強調“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種預設的研究結論,或是某種一定要達成的目標,往往會對客觀分析史料,合理審視歷史事實,造成嚴重傷害”、“歷史的發展,是有正常倫次的。文獻記載若是嚴重背戾這樣的倫次,就要反過來審視這一文獻本身是否存在問題,或者是我們的解釋出現了差誤”,同時,他秉持一種嚴格的實證主義方法,摒棄那些“想當然的猜想”。這樣,他通過對文獻材料的縝密考證和推斷,證明早期的石刻拓印技術、隋代的所謂“摸書”、張秀民主張的唐代貞觀年間即發明雕版印刷的觀點,以及一些學者將唐代元稹文章中提到的“模勒”視為雕版印刷的看法,都是孤立而不可信的。
這背后的邏輯是無懈可擊的:任何重大發明都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它在生成的過程中會留下許多“痕跡”。印刷術不是“一項”技術,而是在許多項技術的基礎上,通過“舊元素的新組合”才得以演化出來的。這其中至少包括:木石或金屬材料上雕刻文字、供印刷用的紙張或絹布、印泥(墨),但最重要的,則是發明這一技術的那個社會的內在驅動力,簡言之,人們為什么要發明它?
這無疑是個重大問題,但也同樣引起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對那些試圖捍衛中國對印刷術發明權的學者們來說,常慣于將鈐蓋印章和制作碑石拓片視為印刷術的“先驅”。在1949年后的很長時間里,很多學者還因受政治環境影響,而將印刷術的起源歸為“勞動人民的偉大發明”,強調這是由庶民需求的通俗文學或日常生產生活實用印刷品推動產生的。但辛德勇認為,這都是難以成立的,因為用印璽“印紙”與用雕版來“印刷”,看似接近,卻不是一回事,因為中國的印信是用作信用憑證而非出于廣泛流布的目的制作的材料;相反,他認為只有佛教密宗信仰那種“大量制作經文來念誦供養,以獲得功德福報”的觀念,才是雕版印刷產生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驅動力。不僅如此,他進而認為,“中國的印刷術,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術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換句話來說,即印刷術源出于印度”,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印度在約7世紀中葉出現的捺印方法。
這樣看來,印刷術僅僅是在輸入中國之后遇到了更適合的社會土壤而獲得大發展,但本身并非產生于中國社會,一如活字印刷源于中國而在西歐發揚光大。不過,在此需要討論的一點是:“印刷術”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在迄今未曾見到印度有早期印刷品出土的情況下,印度那樣捺印于沙或絹紙是否可算作是成形的印刷術?打個或許不恰當的比方,汽車的發明者一般公認是德國人卡爾路本茨,但組成汽車的關鍵部件如輪子、輪胎等根本就不是德國人發明的,在他之前也有英法等國科學家的實驗和設想,甚至內燃機和四沖程工作循環原理也都別人發明或提出的,本茨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創制出第一臺二沖程試驗性發動機,最后將一輛三輪機動車申請專利而被視為汽車的發明者。甚至被視為西方印刷術發明者的古騰堡,現代學者也發現他僅是把原有熟悉的技術轉化為一套新程序,并首先將之做成一項產業而已。在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也不為過。
事實是,由于印度長期不能自行造紙,印刷術從未在古代印度盛行過。在此我們可以補充東南亞地區和藏區的狀況:在東南亞的小乘佛教地區,古代使用的是不適合印刷而只能手抄的貝葉經;而藏區雖盛行密宗,但強調的是師徒口傳而非印經的傳統,加之缺少木材等原料,藏區的印刷術(如德格印經院)是很遲才由漢地輸入的。更進一步說,印刷術所需要的廣泛讀寫能力,恐怕本身是與印度這樣森嚴的等級社會不相容的。凡此均可證明印刷術難以、或竟不可能在當地社會條件下自發產生并扎根發展。
或許可以說,這些意味著,辛德勇先生在設想中仍假定了有單一的真相存在并可去探究。正因此,他最終將發明權歸于印度,至于由這單一起源中心向外擴散的傳播,他大膽推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玄策和義凈將其傳入中國的”。然而麻煩之處,這一傳播路徑的推測沒有任何文獻可資證明;同時,也與他引證的季羨林觀點矛盾:季氏確認:直至王玄策和義凈入印,當地都只是從域外輸入紙張,無法普遍使用紙張作為書寫載體,“從而也就無法在印度當地引發印刷技術”。或許更可取的方法是:既然這一技術的發明是一個社會過程,我們不如反過來去討論促使它得以誕生的那些最適合社會條件——當然,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思中國為何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卻始終未能發展它。
順便說一句,辛德勇先生在書中不僅考證縝密,且持論辛辣犀利無比,批評前人治學之失時絕不留情面,而以“求真”為唯一目標。他多次強調“即使是天大的權威,也不會屈從”,也無人能“代表這個國家的所有學者和公民”為學術研究下定論。有時似不無反應過激之嫌。不過無論如何,對國內學界而言,這樣的獅子吼恐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銷售人員應具備的七種常規武器
傳統印企轉型數字印刷需把握時機
攀鋼研究院開發油墨專用鈦白新產品
影響油墨干燥的幾個要素
故宮養心殿玩起VR技術 個性化十足!
圖文快印企業戰略管理如何進行實施?
發文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型 國務院《意見》圖解
柔性版印刷工藝技術之要點(下)
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僅僅是對這種科學技術發明或其社會傳播過程的客觀論述,因為長久以來,“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一直是我們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無人敢于質疑這一神主牌,相反,正如在其它諸多科技發明的論述中時常見到的那樣,國內學者通常會習慣性地加上一句“比西方早了若干年”這一短語來增強我們一度受損的自信心。
由于結論已經預設好,因此人們常常無暇去仔細推敲每個細節證據,稍有一點能和預設結論相聯的資料,都被迫不及待地拿來作為支撐那個龐大架構的材料。這在心理學上稱之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bias),即當你相信一個事物之后,就會主動尋找能夠增強這一信念的信息。這有時還會導致一種奇怪的現象,就像在西方學者質疑“馬可路波羅究竟是否到過中國”(更多是為了通過這一設問來展開相關問題的討論)時,為這位信口開河的意大利探險家竭力辯護的卻是中國人,原因恐怕或多或少是因為他已被視為“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那他就非到過中國不可。印刷術研究也不例外,一如書中所言,“在研究印刷術起源問題時,有相當一批人都是以捍衛中國人的發明權作為研究目的”。
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吳魯旺(den-nish.wrong)曾說的,脫離了問題,答案是沒有意義的。但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中,人們往往太過注重“答案”而很少去想“問題”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于論證的過程也是走過場,因為他心里已經有答案了。這在學術研究中造成了一系列遺留至今的問題,諸如:先入為主的預判或“定調”;想當然的設想、推導,而忽略邏輯論證;樂于采信符合自己預期的薄弱證據乃至錯誤論證,但忽視或淡化對自己結論不利的證據;采納不夠可信的第二手、第三手文獻,甚至將明知已被證偽的材料仍用作論據,只因這些有利于推導出自己的結論;只看孤證,而不顧及深遠的歷史驅動力及其邏輯性;急于自樹新見,而缺乏與學術共同體的對話,甚至在遭遇質疑后仍各執己見……凡此等等,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都可找到。辛德勇先生在書中多次強調受“正規文史訓練”的重要性,但這些問題的根源或許更可能是思維定式,以及國內文史訓練注重解讀材料而偏廢純理性的邏輯思辨。
書中關于銅活字的考證在這方面可謂典范。辛氏以扎實的文史功底,證明所謂明代銅活字印書,其實根本沒有任何可靠記載,“事實上根本無法認證它的存在”,而我們理應承認朝鮮在活字印刷上比中國先進。在此,他詳細辨析了古籍中“活字銅板”、“銅板活字”和“銅板”等記載,主張這只能解讀為是“活字印本在印制時采用了銅質版片來承放字釘,而根本沒有涉及字釘的材質;據此推定的所謂明銅活字印本,當然完全不能成立”。在此,考證在摧破舊說的過程中,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批評方法。
在以往對這類發明權的研究中,還存在一個不自覺的傾向,即“越早越好”。盡管這有時也是與學者們對材料的不同解讀所致,但恐怕也是這種心態才促使人們去相信一些不可靠的孤證。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辛德勇反復強調“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種預設的研究結論,或是某種一定要達成的目標,往往會對客觀分析史料,合理審視歷史事實,造成嚴重傷害”、“歷史的發展,是有正常倫次的。文獻記載若是嚴重背戾這樣的倫次,就要反過來審視這一文獻本身是否存在問題,或者是我們的解釋出現了差誤”,同時,他秉持一種嚴格的實證主義方法,摒棄那些“想當然的猜想”。這樣,他通過對文獻材料的縝密考證和推斷,證明早期的石刻拓印技術、隋代的所謂“摸書”、張秀民主張的唐代貞觀年間即發明雕版印刷的觀點,以及一些學者將唐代元稹文章中提到的“模勒”視為雕版印刷的看法,都是孤立而不可信的。
這背后的邏輯是無懈可擊的:任何重大發明都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它在生成的過程中會留下許多“痕跡”。印刷術不是“一項”技術,而是在許多項技術的基礎上,通過“舊元素的新組合”才得以演化出來的。這其中至少包括:木石或金屬材料上雕刻文字、供印刷用的紙張或絹布、印泥(墨),但最重要的,則是發明這一技術的那個社會的內在驅動力,簡言之,人們為什么要發明它?
這無疑是個重大問題,但也同樣引起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對那些試圖捍衛中國對印刷術發明權的學者們來說,常慣于將鈐蓋印章和制作碑石拓片視為印刷術的“先驅”。在1949年后的很長時間里,很多學者還因受政治環境影響,而將印刷術的起源歸為“勞動人民的偉大發明”,強調這是由庶民需求的通俗文學或日常生產生活實用印刷品推動產生的。但辛德勇認為,這都是難以成立的,因為用印璽“印紙”與用雕版來“印刷”,看似接近,卻不是一回事,因為中國的印信是用作信用憑證而非出于廣泛流布的目的制作的材料;相反,他認為只有佛教密宗信仰那種“大量制作經文來念誦供養,以獲得功德福報”的觀念,才是雕版印刷產生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驅動力。不僅如此,他進而認為,“中國的印刷術,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術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換句話來說,即印刷術源出于印度”,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印度在約7世紀中葉出現的捺印方法。
這樣看來,印刷術僅僅是在輸入中國之后遇到了更適合的社會土壤而獲得大發展,但本身并非產生于中國社會,一如活字印刷源于中國而在西歐發揚光大。不過,在此需要討論的一點是:“印刷術”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在迄今未曾見到印度有早期印刷品出土的情況下,印度那樣捺印于沙或絹紙是否可算作是成形的印刷術?打個或許不恰當的比方,汽車的發明者一般公認是德國人卡爾路本茨,但組成汽車的關鍵部件如輪子、輪胎等根本就不是德國人發明的,在他之前也有英法等國科學家的實驗和設想,甚至內燃機和四沖程工作循環原理也都別人發明或提出的,本茨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創制出第一臺二沖程試驗性發動機,最后將一輛三輪機動車申請專利而被視為汽車的發明者。甚至被視為西方印刷術發明者的古騰堡,現代學者也發現他僅是把原有熟悉的技術轉化為一套新程序,并首先將之做成一項產業而已。在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也不為過。
事實是,由于印度長期不能自行造紙,印刷術從未在古代印度盛行過。在此我們可以補充東南亞地區和藏區的狀況:在東南亞的小乘佛教地區,古代使用的是不適合印刷而只能手抄的貝葉經;而藏區雖盛行密宗,但強調的是師徒口傳而非印經的傳統,加之缺少木材等原料,藏區的印刷術(如德格印經院)是很遲才由漢地輸入的。更進一步說,印刷術所需要的廣泛讀寫能力,恐怕本身是與印度這樣森嚴的等級社會不相容的。凡此均可證明印刷術難以、或竟不可能在當地社會條件下自發產生并扎根發展。
或許可以說,這些意味著,辛德勇先生在設想中仍假定了有單一的真相存在并可去探究。正因此,他最終將發明權歸于印度,至于由這單一起源中心向外擴散的傳播,他大膽推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王玄策和義凈將其傳入中國的”。然而麻煩之處,這一傳播路徑的推測沒有任何文獻可資證明;同時,也與他引證的季羨林觀點矛盾:季氏確認:直至王玄策和義凈入印,當地都只是從域外輸入紙張,無法普遍使用紙張作為書寫載體,“從而也就無法在印度當地引發印刷技術”。或許更可取的方法是:既然這一技術的發明是一個社會過程,我們不如反過來去討論促使它得以誕生的那些最適合社會條件——當然,由此我們也可以反思中國為何雖然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卻始終未能發展它。
順便說一句,辛德勇先生在書中不僅考證縝密,且持論辛辣犀利無比,批評前人治學之失時絕不留情面,而以“求真”為唯一目標。他多次強調“即使是天大的權威,也不會屈從”,也無人能“代表這個國家的所有學者和公民”為學術研究下定論。有時似不無反應過激之嫌。不過無論如何,對國內學界而言,這樣的獅子吼恐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銷售人員應具備的七種常規武器
傳統印企轉型數字印刷需把握時機
攀鋼研究院開發油墨專用鈦白新產品
影響油墨干燥的幾個要素
故宮養心殿玩起VR技術 個性化十足!
圖文快印企業戰略管理如何進行實施?
發文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型 國務院《意見》圖解
柔性版印刷工藝技術之要點(下)
上一篇:百雀羚營銷引發的大討論
下一篇:淺談數碼印刷中的幾個大問題